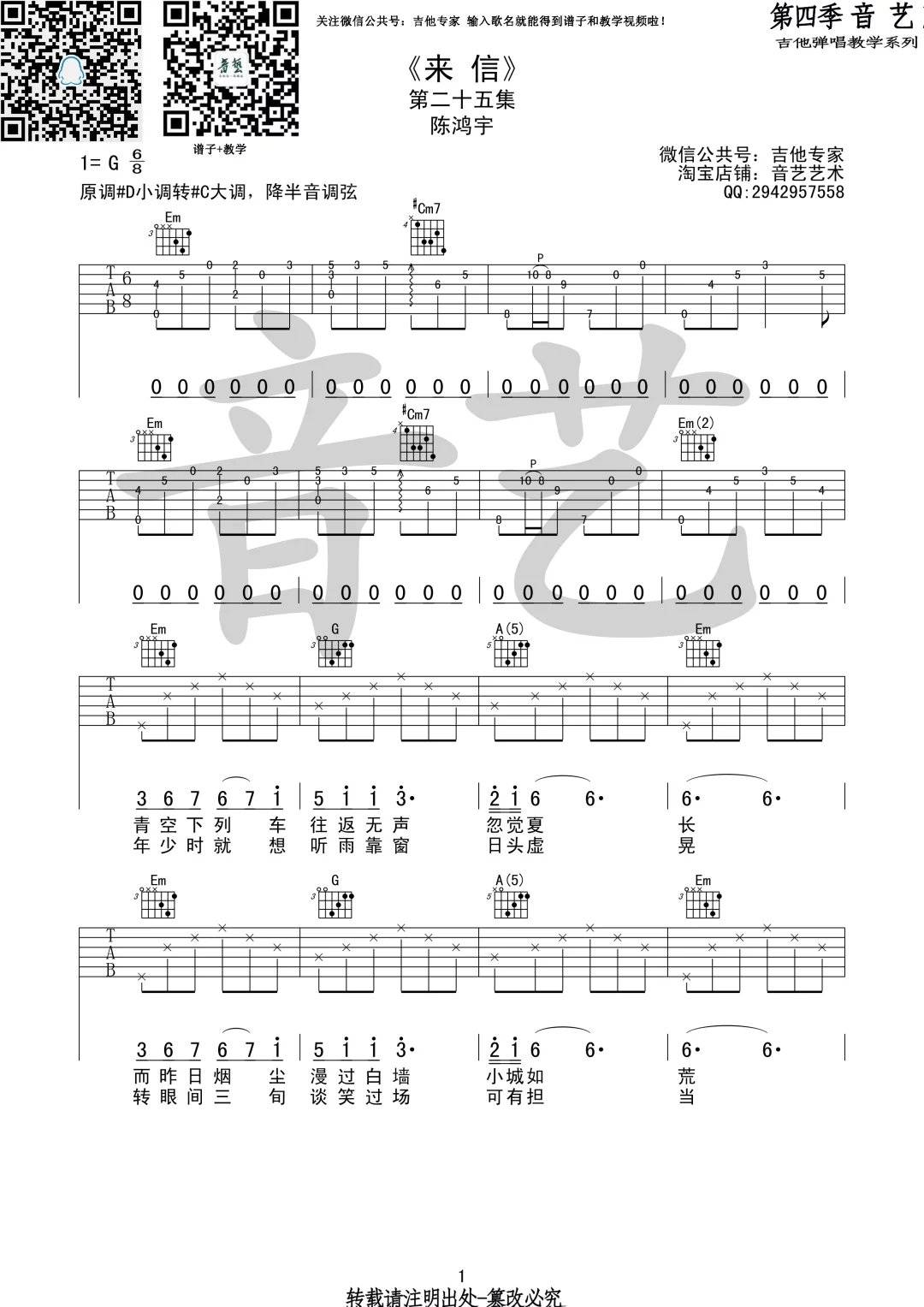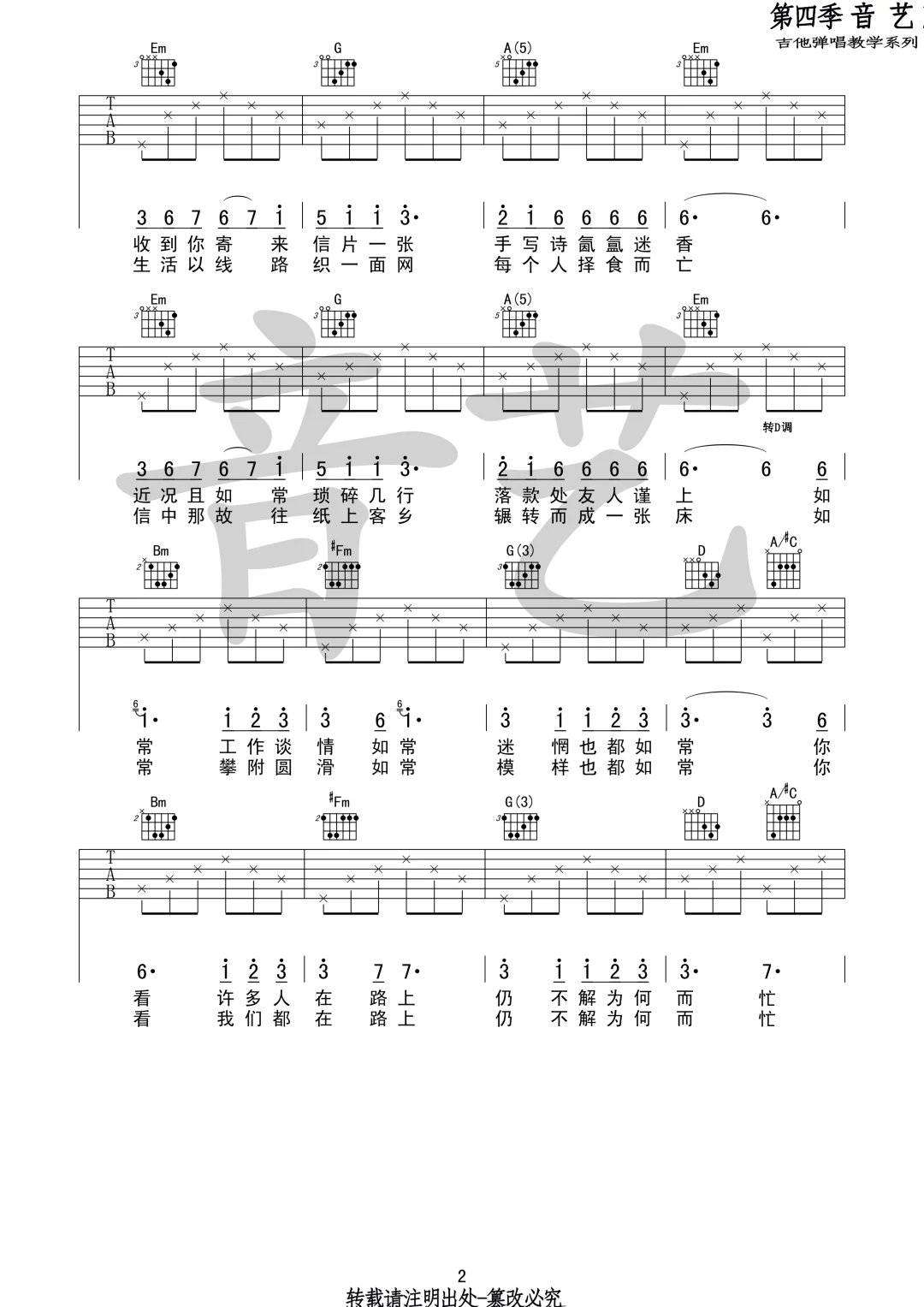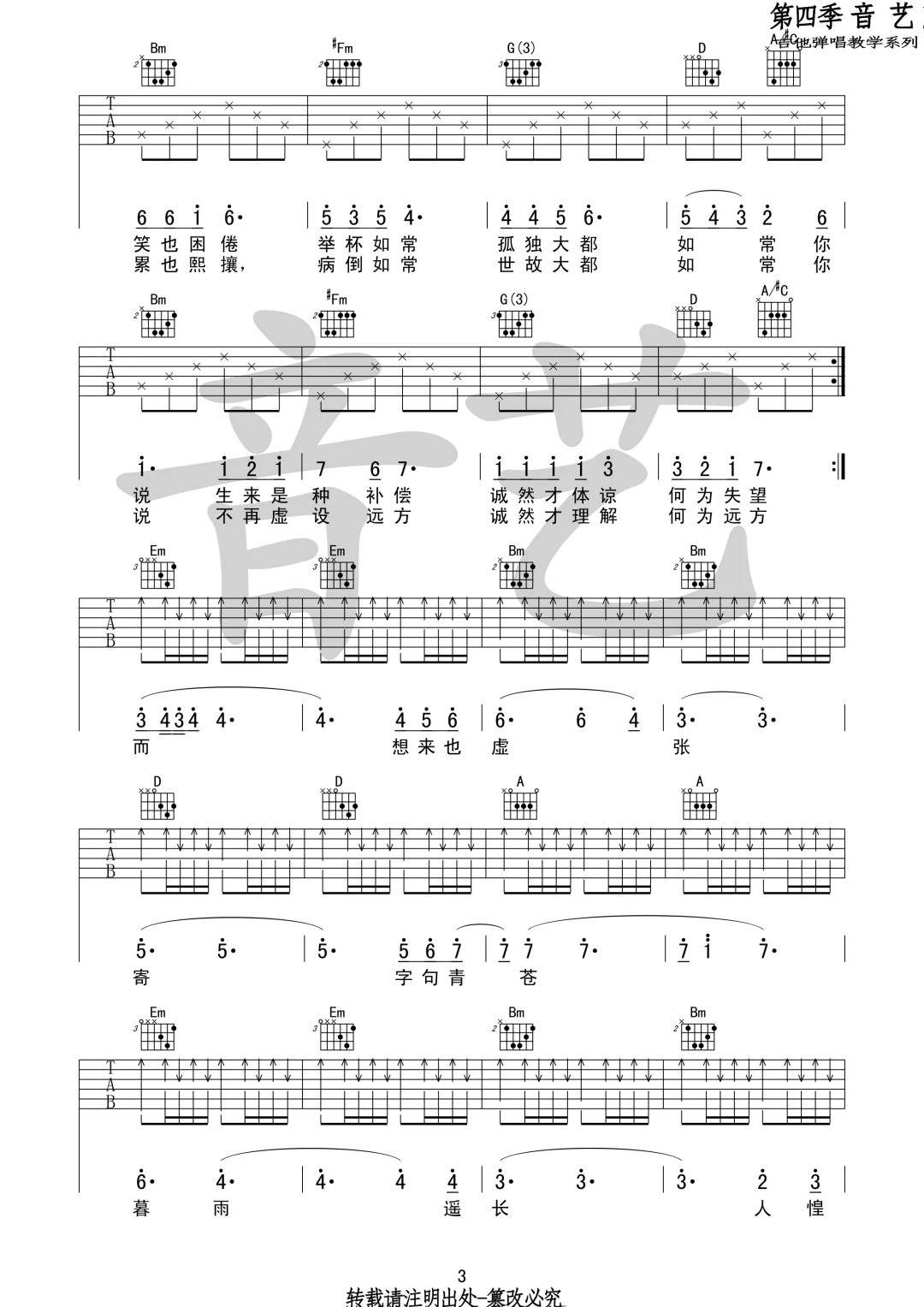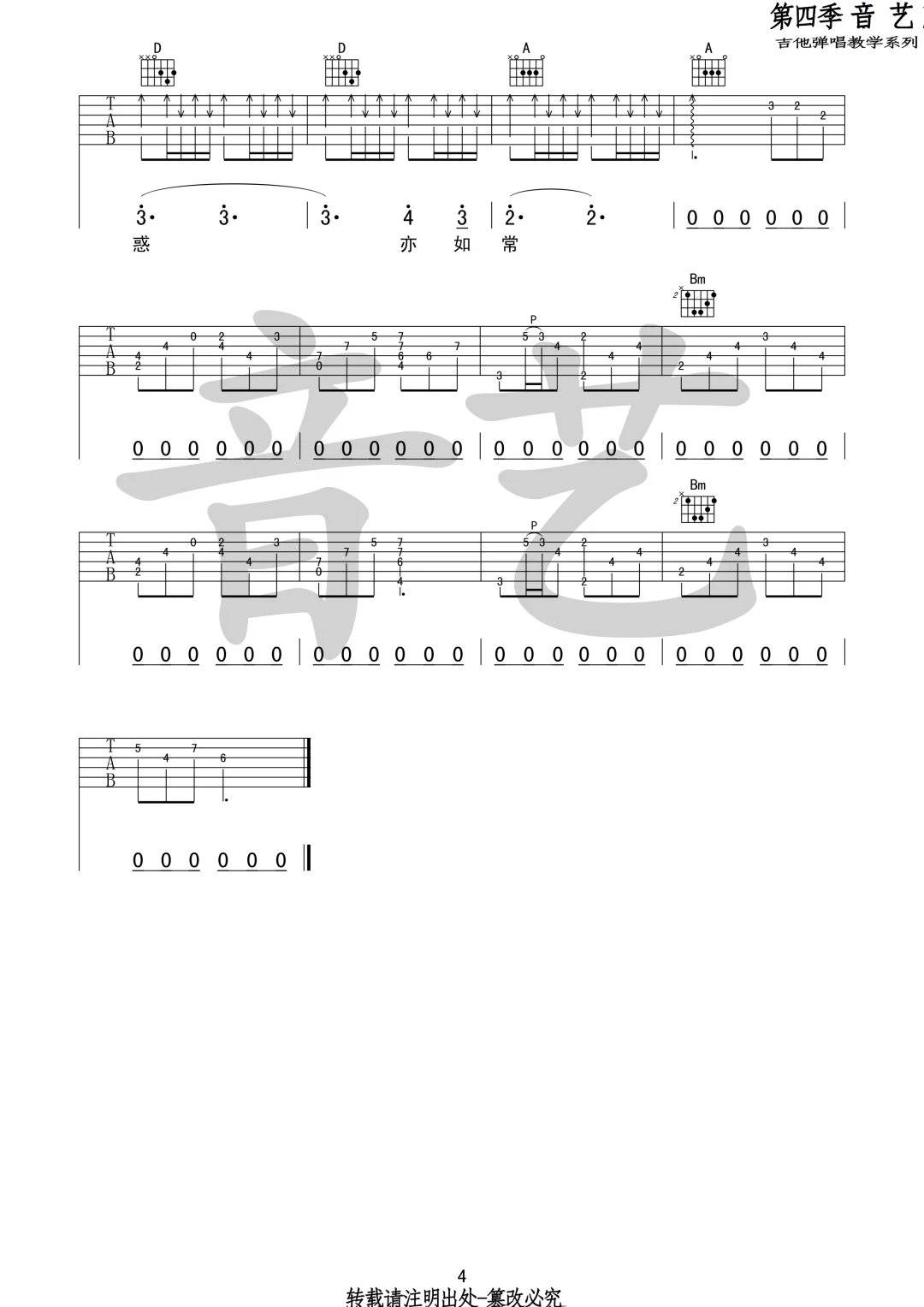《来信》以纸笔为媒构筑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将未寄出的书信化作情感的容器。泛黄信笺上凝固的墨迹成为记忆的标本,折痕里藏着欲言又止的顿挫,邮票锯齿边缘咬合着等待的焦灼。邮戳上的日期永远停驻在某个黄昏,信纸背面透出的字痕暗示着被反复修改的心事。这种具象化的思念载体,让抽象的情感获得了可触摸的质地。信封上的地址在多年后成为失效的密码,收件人姓名却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笔触,如同某种固执的仪式感。信纸展开时簌簌的声响替代了言语的颤抖,钢笔洇开的蓝色墨团成为情绪溃堤的证明。那些被划掉的词句在纸张纤维里继续生长,构成真实于文字的潜台词。邮筒的金属内壁反射着无数未完成的告别,投递口如同时间吞噬记忆的豁口。当电子讯息取代了纸页摩挲的质感,这首歌词重新打捞起书信时代特有的延迟美感——那种在投递与接收之间发酵的期待,那种在字句推敲中沉淀的郑重。最终未被拆封的信件成为自洽的情感闭环,寄信人其实早已在书写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