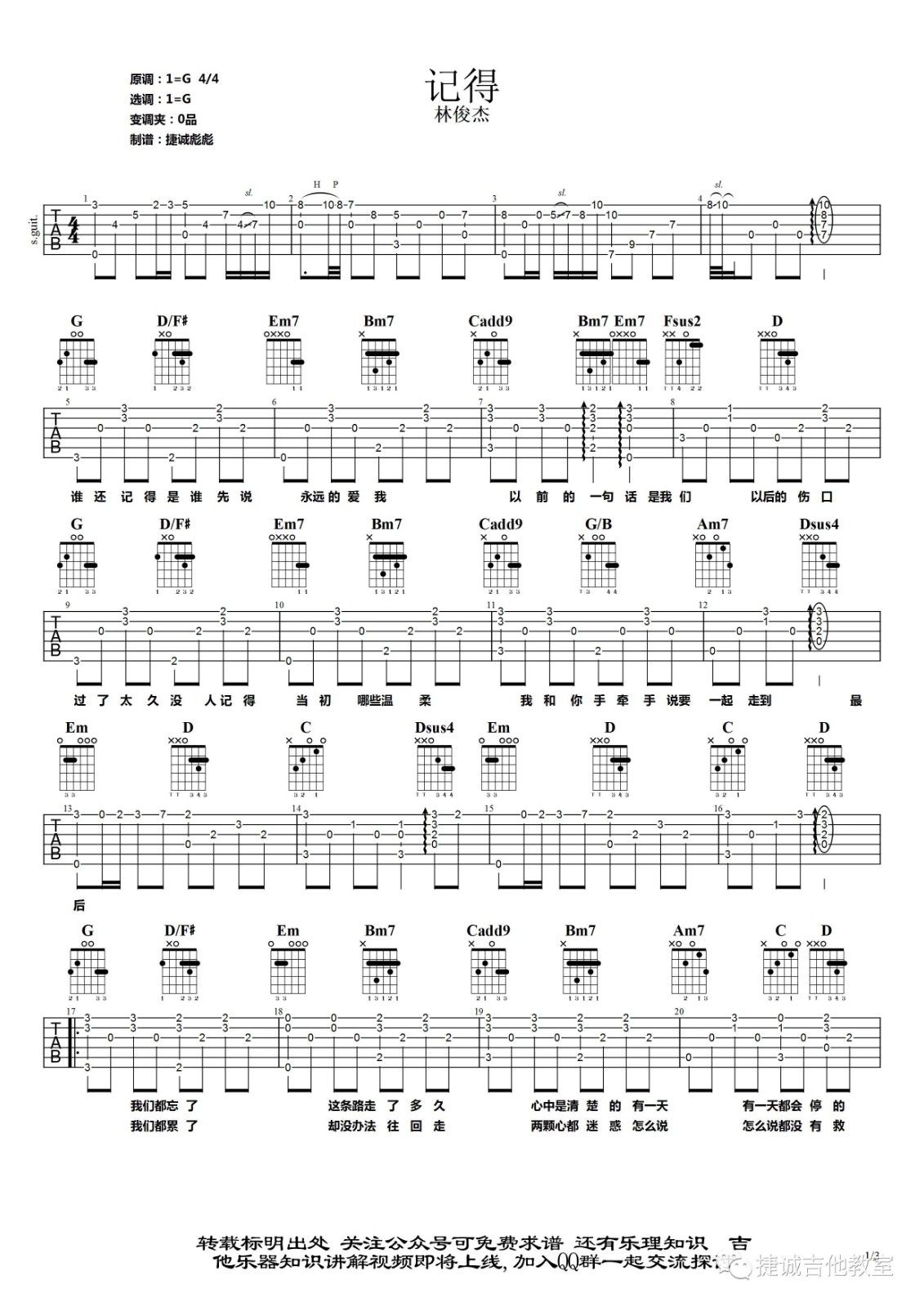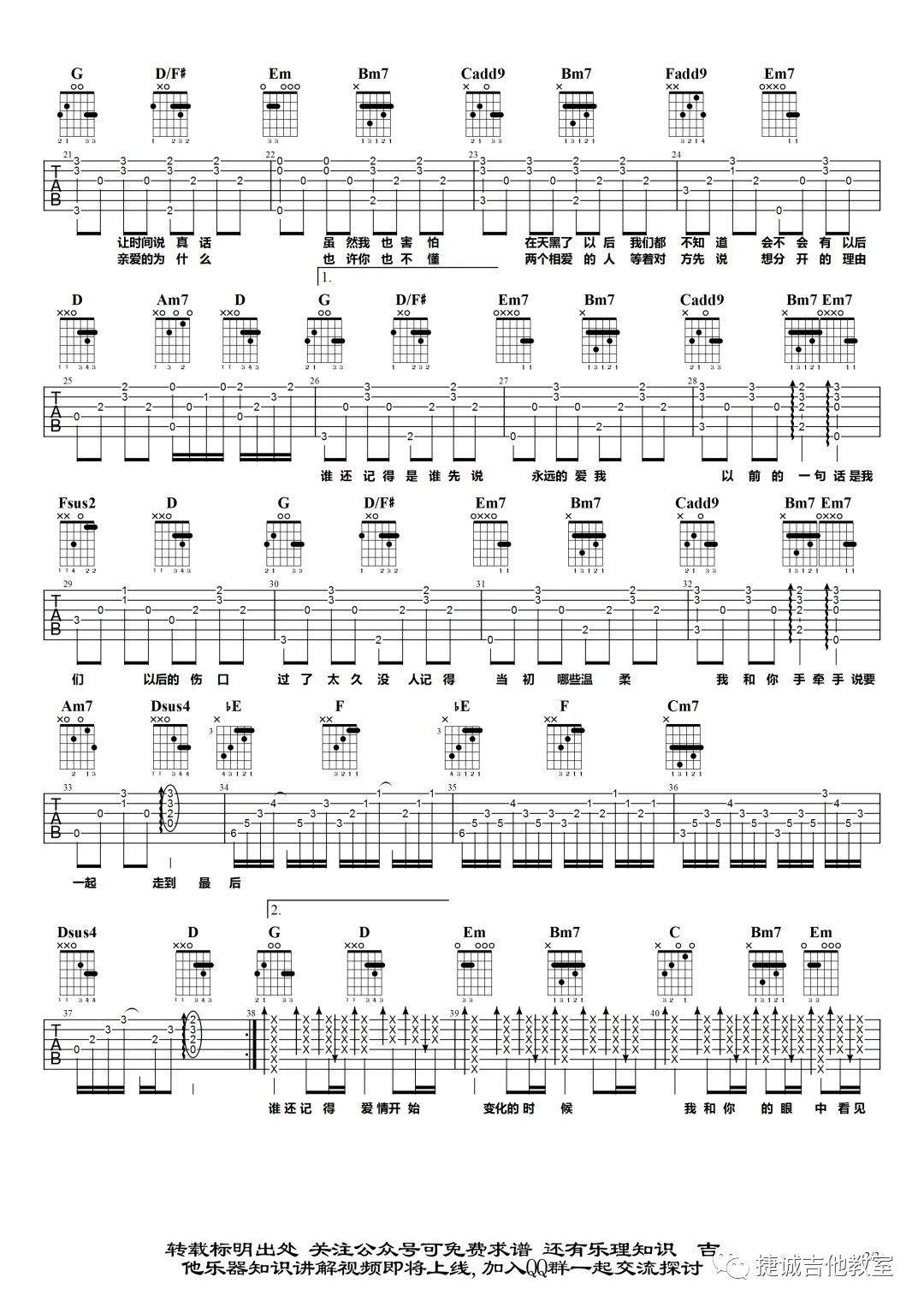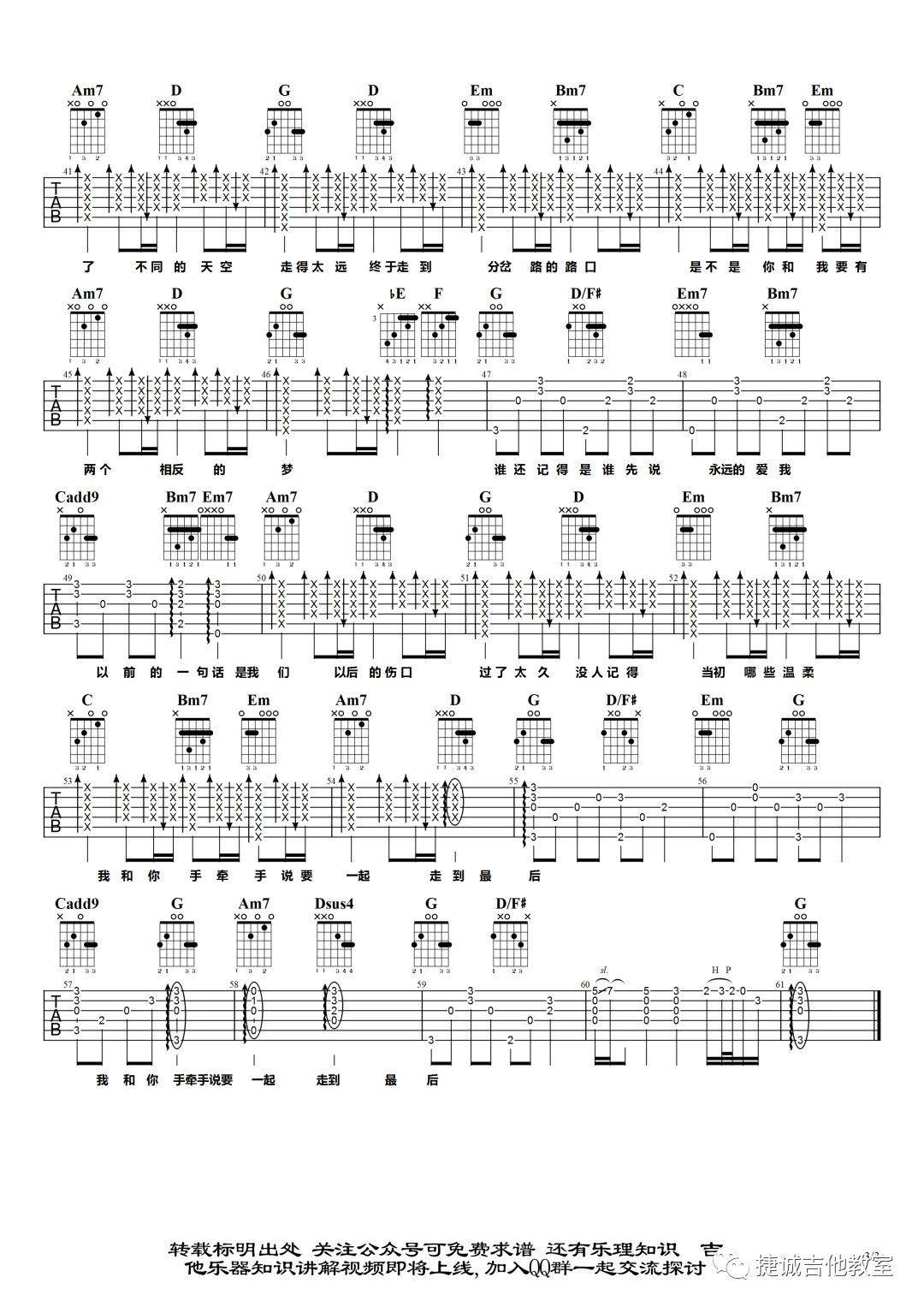《记得》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记忆在时间洪流中的脆弱与永恒,通过具象的生活片段展现人类情感的共通困境。歌词中"褪色的明信片"与"生锈的八音盒"等意象构成记忆的物质载体,暗示物理存在与情感记忆的悖论——器物会腐朽,而某个雨天的气息或指尖温度却能在意识中长久鲜活。这种矛盾延伸至人际关系层面,"你笑着说再见的弧度"与"转身时颤抖的肩线"形成表情与身体的叙事分裂,揭示记忆的选择性留存往往不取决于场景的完整性,而取决于瞬间的刺痛感。时间在歌词中被塑造成双重角色,既是溶解记忆的溶剂,又是结晶情感的催化剂,那些"以为忘记的晨光"会在某个相似的黄昏突然复苏,证明遗忘不过是记忆的另一种储存形式。城市空间的变迁成为记忆的对照组,重建的咖啡店与消失的梧桐树构成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冲突场域,当歌词追问"是我们改变了场景,还是场景改变了我们"时,实际上在探讨记忆如何通过不断的重构来维系自我认同的连续性。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辩证的记忆观:真正被遗忘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,而是事件发生时那个版本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