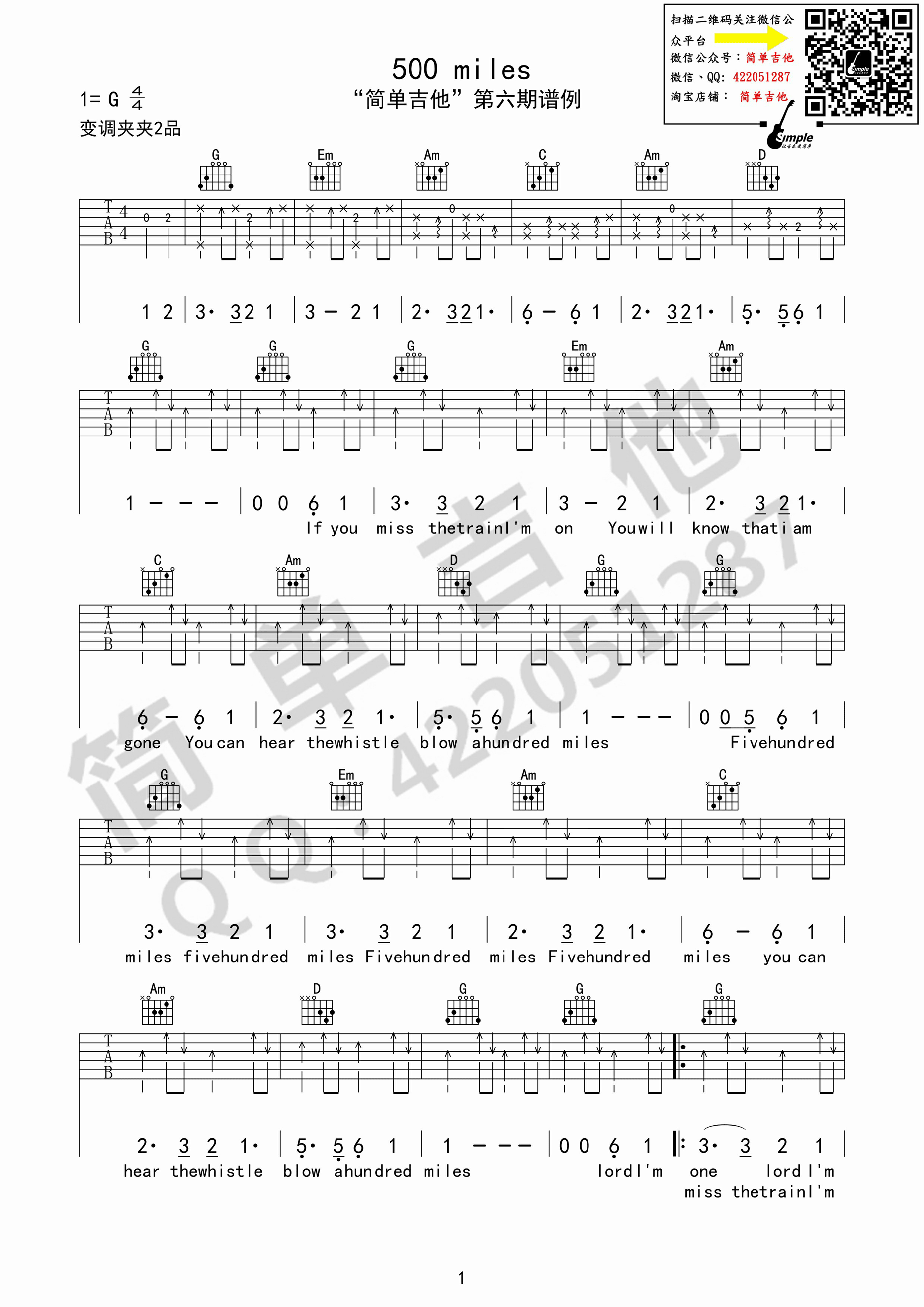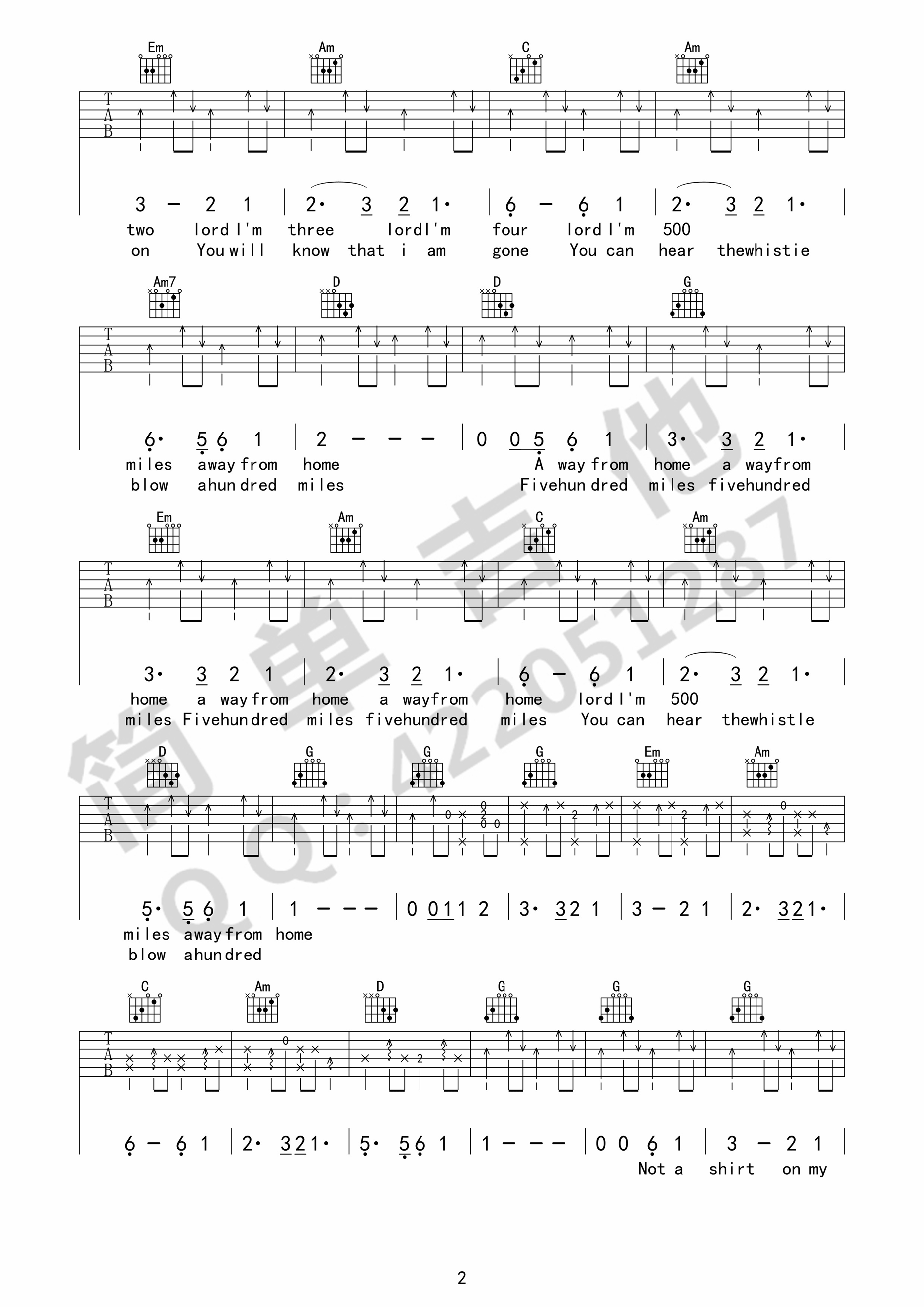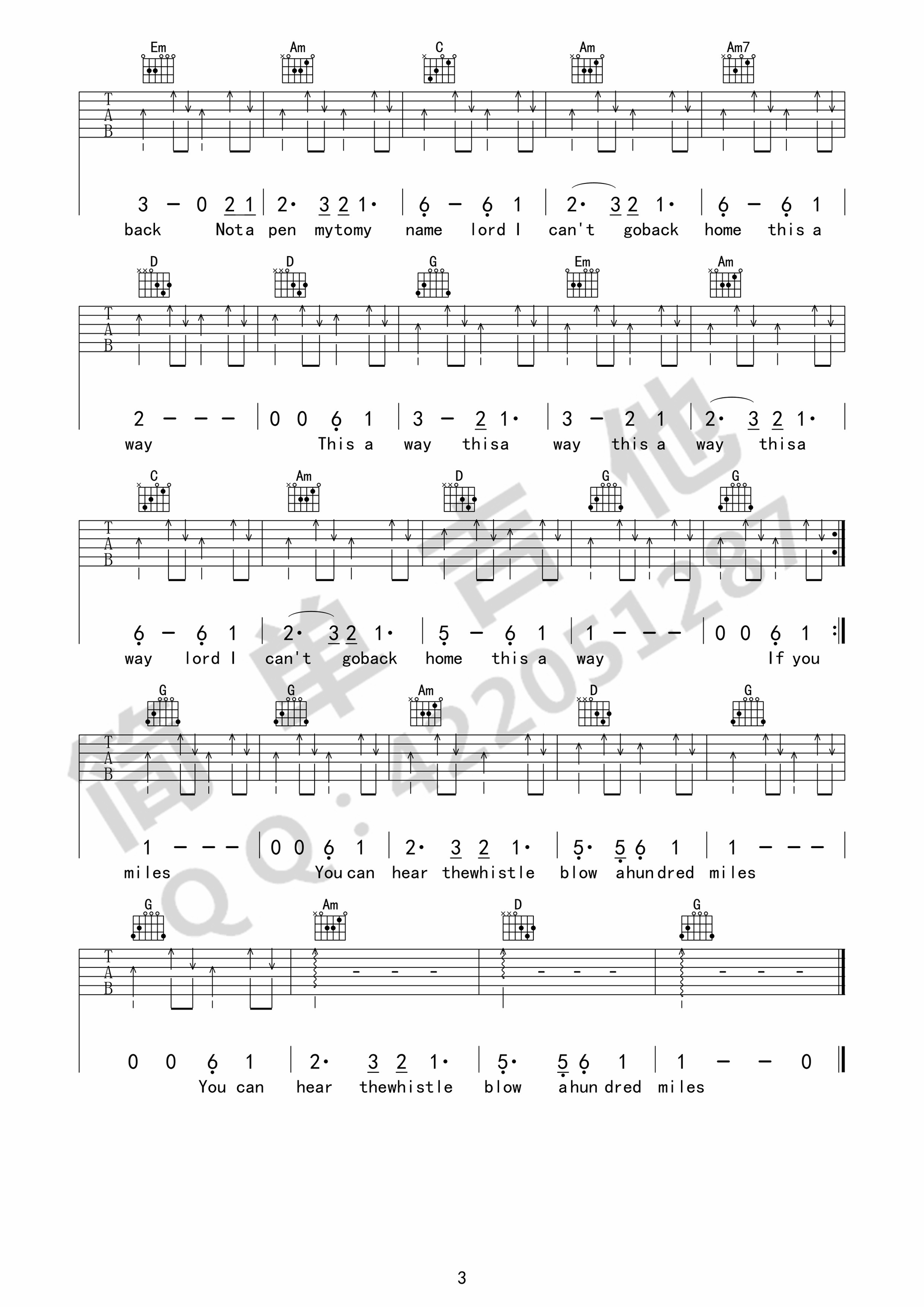《500 miles》以简洁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漂泊者与故乡之间永恒的情感纽带。歌词中重复出现的“五百英里”既是地理距离的丈量,更是心理距离的象征,铁轨的意象串联起空间位移与时间流逝的双重轨迹。蒸汽火车喷吐的煤烟与衬衫上的破洞构成物质匮乏的具象表达,而“上帝啊我已漂泊五百里”的反复咏叹则升华为精神层面的集体共鸣。歌词通过“不能归去”的克制陈述,道出了流浪者群体的生存困境:当物理距离超过某个临界值,故乡就变成了需要经济资本才能抵达的奢侈品。硬币在空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细节,暴露出工业化时代个体在物质与精神间的撕裂状态。火车汽笛声既是出发的号角,也是乡愁的催化剂,铁轮与钢轨的撞击节奏暗合着心跳频率,使交通工具本身成为移动的乡愁载体。歌词未言明的留白处,藏着无数个背井离乡者的共同记忆——那些为了生存被迫迁徙的无奈,以及被距离重新定义的亲情关系。最终,“五百英里”的复沓形成了一种宿命般的循环韵律,暗示现代人的漂泊已成为常态,而故乡永远停留在无法折返的远方。